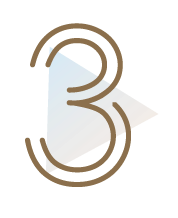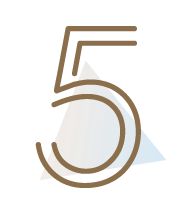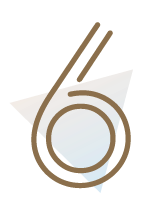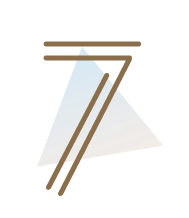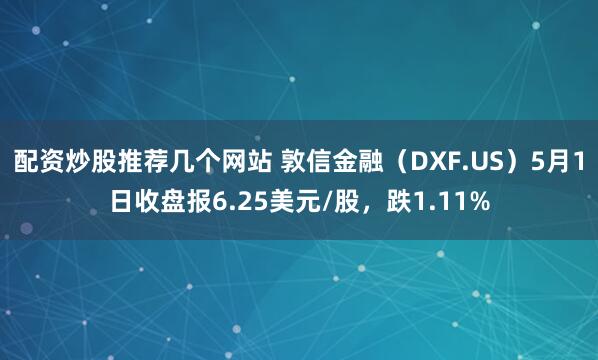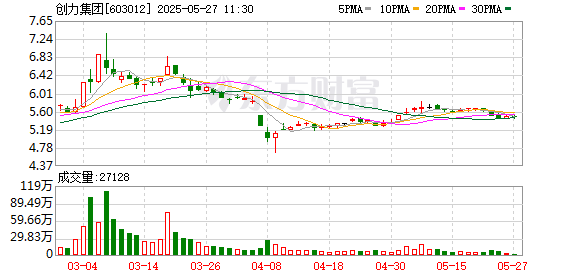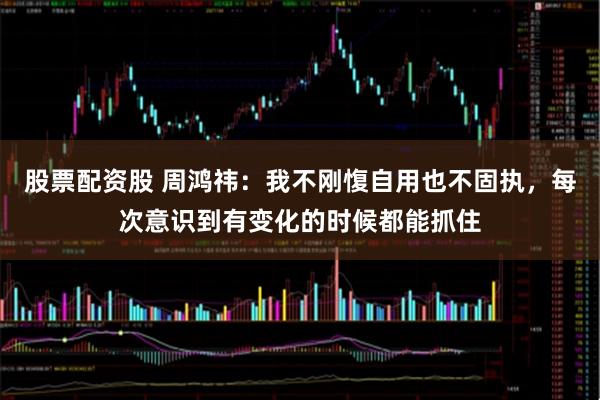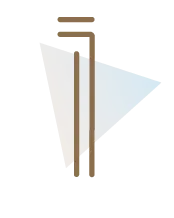
美国债务问题概览
1. 债务与财政赤字的核心数据
刘波首先就直击关键数据:美国联邦政府总债务已达36.22万亿美元,其中公共债务(外部投资者持有部分)29.03万亿美元,政府内部债务(如美联储持有)7.19万亿美元。
刘波指出,公共债务是真正需要警惕的部分,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国际投资者对美债的信心。
美国在财政赤字方面,累计规模达1.3万亿美元,而2025年联邦净利息支出将占预算开支的13%-14%,根据刘波分析,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国防与医疗保险的支出,成为美国财政的“刚性负担”。
换句话说,每1美元的财政支出中,有越来越多被用于还旧债,而非投入教育、基建等具有潜在生产性效益的领域。
2. 国际评级机构的预警信号
2025年5月,国际评级机构穆迪(Moody's Ratings)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1,这是继2011年标普、2023年惠誉之后,第三家对美国评级“降级”的机构。
对此,刘波分析认为,评级的下调并非否定被评级对象的当下偿债能力,而是对其远期可持续性存在担忧,这也意味着作为全球安全资产标杆的美债,正在失去绝对的信任背书。
3. 定性:困局而非危机
刘波强调,美国债务当前是已有“隐忧”而非身处“危机”。美债收益率未出现失控性飙升,国际投资者虽有减持(如中国、日本适度抛售),但未形成全面抛售潮。穆迪下调评级更多是对长期信心的削弱,这并非当下已经失控的信号。
不过,一定要注意的是,美国债务的长期风险不容忽视。穆迪预测,2035年美国债务占GDP的比例将升至134%,财政赤字占比攀升至9%;刚性支出(如利息、社保、医保)占总支出比例将从73%升至78%,这意味着预算的灵活性将会持续萎缩,更进一步,未来可用于经济增长的“生产性支出”的空间将被进一步挤压。
达利欧的债务周期模型
1. 理解债务周期的基础:信贷的双面性
信贷是市场经济的“血液”,也是债务的源头。刘波解释,信贷的本质是提前透支未来收入,企业通过信贷获得启动资金扩大生产,居民通过信贷来购房或消费。
一个人的支出是另一个人的收入,从这个角度来说,信贷扩张会带动经济繁荣,就像企业借100万投入生产,若盈利130万,连本带息偿还120万后仍赚10万,这就是信贷的正向循环。
但信贷的另一面是逃不掉的债务,若企业盈利不及预期(如上述案例中仅赚110万),偿债压力会挤压其再投资与员工薪资,进而影响上下游企业,形成连锁反应。
因此,信贷与债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,共同构成驱动经济周期性发展的核心驱动力。
2. 短债务周期 VS 长债务周期
达利欧将债务周期分为两类:
短周期:持续约6年,由利率调控驱动。经济低迷时,央行会采取降息的手段来刺激信贷,导致资产价格推高与通胀;当通胀超过理想水平,央行又会加息以抑制信贷,导致经济放缓,形成“扩张-收缩”循环。
长周期:由多个短周期叠加而成,债务规模呈螺旋上升趋势。在短周期中,债务规模虽有波动,但整体呈上升趋势;而进入长周期的后期,债务就会像“血管中的斑块”一样持续积累,最终可能引发经济社会的“心脏病”,如银行挤兑、债务抛售等突发性危机。
达利欧用比喻形象说明,在长周期中,债务积累到临界点后,任何外部冲击(如地缘冲突、政策失误)都可能触发危机,就像血管斑块破裂一般迅速引发心梗。
3. 债务危机的应对:两种减债路径
政府应对债务危机有两类核心手段:
通缩型减债:债务重组(延长还款期限)或核销(减免部分债务),直接把债务人负担降低,但这样做会导致债权人遭受损失,如美债持有者若遭遇重组,他们的本息收益将严重缩水。
通胀型减债:通过印钞制造通胀,稀释债务的实际价值,这是各国更常用的方式。若通胀率6%,而美债利率5%,债权人实际收益其实为负,相当于债务人变相地少还了一些钱。”
达利欧指出,这两种方式各有代价:通缩型减债可能引发经济紧缩,通胀型减债则会损害货币信用。
4. 债务本身不是坏事
关于债务本身的性质和影响,刘波一直强调债务本身不是坏事,关键是要看债务的用途与当下所处的周期位置。
刘波举例,政府发债修建公路可以直接激活一个区域的经济,企业借债投入研发可以助力竞争力的提升,这类“生产性债务”能创造未来收益,属于良性循环。但若是用于单纯支付利息或填补非生产性缺口,则很可能加剧风险。
达利欧看待“经济机器”的独特方式
达利欧提出与传统供需理论不同的价格公式:价格(P)=购买某物的总支出(TE)/总销量(Q)。
以美债市场为例,若投资者愿意投入的总资金(TE)减少,而国债发行量(Q)不变,国债的价格必然就会下跌,收益率则相应上升,这是一种机械性的客观规律,与信心这类主观因素无关。
这一公式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、2010-2012年欧债危机中得到验证。欧债危机时,达利欧发现投资者杠杆率已经逼近了监管的上限,未来购买能力(TE)将萎缩,但欧债发行量(Q)仍在增加,据此得出了价格下跌、收益率飙升的判断,最终精准应验。
传统观点认为,经济危机是信心不足导致的心理现象,所以政府可以通过释放乐观数据来提振市场。
但达利欧的公式揭示,若TE与Q的失衡已成事实,仅靠信心喊话是无法扭转颓势的,就像在欧债危机时,欧盟公布再多所谓的“健康数据”也无法改变投资者资金枯竭的现实。
美国处于大债务周期的什么位置?出路是什么?
1. 周期定位:后期但非危机
刘波分析,目前美国已进入大债务周期的后期,但未必会爆发突发性危机,核心判断依据如下:
风险因素:美国的债务规模庞大(2035年将占GDP的134%)、国民储蓄率低(抗风险能力弱)、刚性支出挤压生产性投入。
缓冲因素:一方面,美债以本币计价,美国可通过印钞缓解压力;另一方面,美元仍是全球储备货币(占60%全球储备),国际需求仍长期存在。
短期看,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尚稳(增长适度、通胀可控),但长期债务对经济活力的侵蚀是确定性趋势。
2. 达利欧的解决方案:3%+三部分
核心目标:将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降至3%(当前约9%)。
三部分措施:
减支:压缩刚性支出(如优化社保、医保结构),但这势必会面临老龄化压力带来的政治阻力,毕竟美国社会已经习惯福利支付,削减支出容易引发民意的反弹。
增收:扩大税基(如向富人增税),但具体执行还需要平衡两党的博弈。民主党主张向富人征税,共和党倾向保护资本,想要二者达成共识并非易事。
低利率环境:通过货币宽松对冲财政紧缩的下行压力,为调整创造空间。虽然财政紧缩抑制需求,但货币宽松能刺激经济活力,以此形成政策的平衡。
美国所处的政经大周期
达利欧认为,各国的政经大周期由五大因素共同驱动:债务/信贷/货币/经济周期、国内秩序周期、国际秩序周期、自然力量(如气候变化)、人类创造性(如技术革新)。
当前,美国的核心矛盾是债务周期后期与国内秩序混乱叠加在了一起。
美国正处于从强盛到混乱的转折期。
刘波指出,美国的两党分歧已经从政策差异升级成了价值观的对立:在气候变化议题上,共和党多持否定态度,民主党则主张激进减排;在“觉醒文化”上,民主党认为是在争取平等,共和党则视之为压制言论自由。
更危险的是政治逻辑的变化。过去,两党虽长期存在分歧,但愿意在关键时刻妥协;如今,政治博弈转向赢家通吃,民主制度的协商基础被大幅削弱。
特朗普代表的极右翼崛起,还有单边主义政策(如加征关税),都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内部撕裂。
长期繁荣让美国社会耽于安逸,传统工作伦理、道德观逐渐受到侵蚀,虚无主义流行。达利欧提醒,对美国而言,当下最大的挑战不是与中国竞争,而是能否重建向上的文化,这是突破周期困局的根本。
美国债务隐忧对他国影响
1. 直接风险:资产冻结与隐性违约
当下,美国面临债务上的隐忧,这对他国最直接的影响是美国可能对其“敌对国家”采取资产冻结(如俄乌冲突中对俄罗斯的措施)、暂停付息等手段。
刘波分析,这会迫使持有美债的国家加速去美元化,如扩大货币互换、使用美元之外的货币结算,这将削弱美元储备地位。
2. 危机传染与滞胀风险
若美债危机叠加银行业危机和金融危机,则可能引发全球外需的萎缩。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,其需求下滑将冲击各出口国。
同时,美联储为应对债务危机可能会更为激进地加息,这将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美元债务偿债压力骤增,继而引发资本外逃、货币贬值和输入性通胀。
3. 封闭化与“两套体系”
面临债务隐忧,美国可能进一步推行“小院高墙”,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技术与投资在全球范围的流动,进一步走向实用主义和美国优先主义,向曾经那个孤立主义、霸权主义主导的时代靠近。
刘波分析,在这种情况下,美国试图构建以美元为主导的“平行体系”:一套是以美国主导的以美元为主的体系,另一套是非美国国家的体系。这会加剧全球经济分裂的情况,就像目前的特朗普关税战,迫使各国在美国体系与非美国体系中选边站。
从本书衍生的开放性思考
1. 债务周期与传统经济周期的关系
达利欧侧重债务驱动,传统经济学则强调总需求不足。在刘波看来,两者并非对立。债务周期是经济周期的货币表现,但需结合就业、消费等因素全面分析,例如凯恩斯主义关注的“总需求”,本质上也受债务扩张与收缩的影响。
2. 债务周期的抽象化争议
过度关注债务规模可能忽视文化与制度差异。刘波举例,中国看重储蓄与美国习惯高消费的习惯就很不一样。中国居民的储蓄率高,在债务的总体结构合理的前提下,债务承受能力更强;美国人更依赖且习惯于借贷消费,同等债务规模下的风险就会更高。总之,债务的影响需要结合具体国情来判断。
3. 乐观派的视角
部分观点认为,“债务占GDP比例”这一指标的参考价值有限,因为流量与存量不可直接对比,且美元储备地位依旧稳固。
只要美债付息能力没有崩溃,国际投资者就仍然会持有,就像1971年尼克松放弃金本位后(本质是违约),美债不仅未遭抛售,反而因流动性优势维持了需求。
4. 现代货币理论的观点
现代货币理论认为,只要债务以本币计价且未引发高通胀,经济就可持续。
美国当前的通胀尚为可控,因此可以继续借债,无需过度担忧债务规模,这一观点与达利欧的“中间派”观点形成了对话。
5. 中国的应对
刘波认为,中国应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、扩大资本账户开放,减少对美元储备的依赖。与此同时,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驱动,降低对美债的间接依赖,只要内需成为了驱动增长的主力,外需波动所造成的影响就会减弱。
总的来说,达利欧的《国家为什么会破产》并非预言危机,而是提供了一种理解经济运行的“周期思维”:从信贷扩张到债务积累,从短周期波动到长周期转折,每个环节都有规律可循。
美国债务困局的启示在于,债务本身无好坏,关键是用途、周期位置与应对智慧。对于每一个普通人股票配资股,理解这些规律不仅能洞察全球经济的可能走向,更能为个人决策提供底层的逻辑支撑。
辉煌优配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